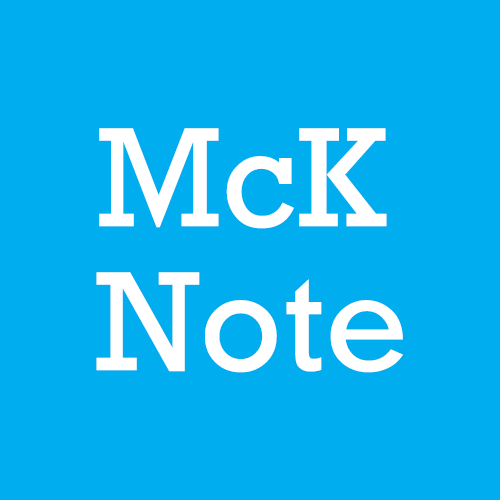直到今天,當我整理起《鳥人》的原聲帶時,還是覺得主角 Riggan 在深夜街頭喝著威士忌的一幕最動人,當時的配樂就是 Maurice Ravel 的 Passacaille (Très large)。但我古典樂懂得不多,只是比一般人常聽一點,所以只能就基本的資訊說文解字。
Passacaille (Très large) 是 拉威爾《A 小調鋼琴三重奏》(Piano Trio)中的第三樂章,其它樂章分別是 I. Modéré、II. Pantoum (Assez vif) 和 IV. Finale (Animé),它們的中文意思分別是:
| 曲名 | 中文意思 |
|---|---|
| I. Modéré | 中版 |
| II. Pantoum (Assez vif) | 潘多姆四行詩(相當活躍的) |
| III. Passacaille (Très large) | 帕薩卡利亞(非常寬廣的) |
| IV. Finale (Animé) | 終曲(生氣蓬勃的) |
其中 Pantoum 是源於一種名為 Pantun 的馬來語詩詞。簡單來說,Pantoum 中每節的二四句為下一節的一三句,拉威爾將第二樂章命名為 Pantoum,自然是暗示了樂曲的編排借鑒了 Pantoum 的格式,至於具體是怎麼運用的,我只有找到一篇題為〈文學形式在音樂中的運用〉的論文,裡面詳細說明了 Pantoum 的規範和樂曲中借鑒的痕跡,有興趣的人可以讀一讀。
至於 Passacaille,中文翻為「帕薩卡利亞舞曲」,是一種類似夏康舞曲(chaconnes)、低音固定、旋律又富有變奏感的曲式,風行於巴洛克時期晚期。Passacaille 這個詞源於西班牙文的 pasacalle,是由 pasar(行走)和 calle(街道)所組成,在十七世紀時,Passacaille 通常用作跳舞和演奏的間奏。除了拉威爾以外,韓德爾、巴哈、布拉姆斯和海頓等人都有出色的 Passacaille 作品,特色各異。
我這幾天密集把《A 小調鋼琴三重奏》惡補了一下,聽的是 Paul Tortelier 的版本,聽到目前的感覺是第一樂章徬徨不安、第二樂章興奮急躁、第三樂章哀傷舒緩、第四樂章柳暗花明。老實說,有時把這四首曲子放著當背景音樂,工作一忙,就會不小心聽漏第三樂章,反而期待第二樂章的到來。要不是先聽過第三樂章,我或許會覺得第三樂章很無聊吧,因為它的低沈真的遠低於其它三個樂章的情緒水平,有的時候聽完第二樂章,會感覺接續下去的是一片無聲,直到末端才聽到一些聲音。為什麼拉威爾會如此創作呢?根據 Wikipedia 上的資料,第三樂章開頭其實和第二樂章的主題(Theme)有關,整首曲子便在鋼琴、大提琴和小提琴的輪轉下緩緩開展。拉威爾在創作時即意識到「如何平衡三者的聲音」將成為創作的關鍵,尤其是如何讓大提琴脫穎而出,並運用了大量的顫音(Trill)、震音(Tremolo)、泛音(Harmonics)、滑音(Glissando)和琶音(Arpeggios)。或許第三樂章的存在不僅僅是為了情感上的鋪陳,而是為了從另一個角度試驗三者的和諧性。
為了驗證這個假説(?),我去找了樂譜來讀。很少讀樂譜的我,照著聽到的聲音一一對照樂譜上的進度,忽然覺得有點感動。我還是按出場順序才確定哪一行是鋼琴、大提琴或小提琴。雖然我沒辦法準確分出上面提到的五種技巧,但在第三樂章中拉威爾「平衡三種樂器」的主要方法應該是分配三種樂器的出場比例和銜接,技巧上倒是比較單純,讓我有反璞歸真的感覺。不過這讓我想到調酒,越簡單的調酒,越講求比例,拉威爾能用簡單的技巧,將三種樂器的出場安排得服服貼貼,非常厲害。Passacaille 成了單純濃郁的苦酒。
如前所述,在《鳥人》中這首曲子搭配的場景,是 Riggan 一個人在深夜喝著威士忌散步的時候,當時他剛和劇評人 Dickinson 吵完架,喝著馬丁尼,背景突然播起了 Passacaille。(題外話,馬丁尼也是一種簡單的調酒,我上酒吧通常會點,但很少喝到真正好喝的。)他散步的時候,路邊有個人喊著《馬克白》的台詞,有人說《鳥人》故事的原型就是《馬克白》,其中 Riggan 是馬克白,鳥人是馬克白夫人,但我沒讀過《馬克白》,沒辦法參透這層意思,倒是可以理解鳥人伊卡洛斯的隱喻。
那一幕之所以打動我,是因為 Riggan 看起來非常落魄,路人的狂野、酒店前花花綠綠的燈飾都反映了這點,而 Passacaille 配得恰到好處,Michael Keaton 的演技更不用說了。如果用第二和第三樂章的關係來解讀這一幕,也頗耐人尋味。前面提到,第二樂章興奮急躁、第三樂章哀傷舒緩,情感上好像不太連貫,但其實第三樂章中不斷重複的旋律,是來自第二樂章的主題,所以興奮和哀傷背後有相通的成分。《鳥人》中,Riggan 的心態和情況也是不斷搖擺,演員失控、女兒發飆、情人懷孕、伴隨著一連串亂七八糟的小事,雖然看起來只是逆境中不斷湧現的酸檸檬,不禁令人猜測背後的聯繫。那麼,是什麼造就了 Riggan 如此哀傷的一幕呢?恐怕也是出於他人格與行為中的狂亂,即鳥人一角大鳴大放後在他心中所留下的原形。當他和 Dickinson 激辯完,不知是否也意識到這點?

最後 Riggan 將自己從不斷搖擺的心態中解救出來,落魄喝酒的 Passacaille 也好,醒來後興奮得飛越紐約市的 Prologue: Chorus of Exiled Palestinians 也好,都成了過去式。最後結束這一切的,是拉赫曼尼諾夫的《E 小調第二號交響曲》,據說這也是拉赫曼尼諾夫走出失意的復興之作。不過 Riggan 迎來的不再是得意和失意間的拉扯,也不用再為兩者之間的共同根源所苦,他所迎來的,是真正的解脫。
圖片來源:AdoroCinema